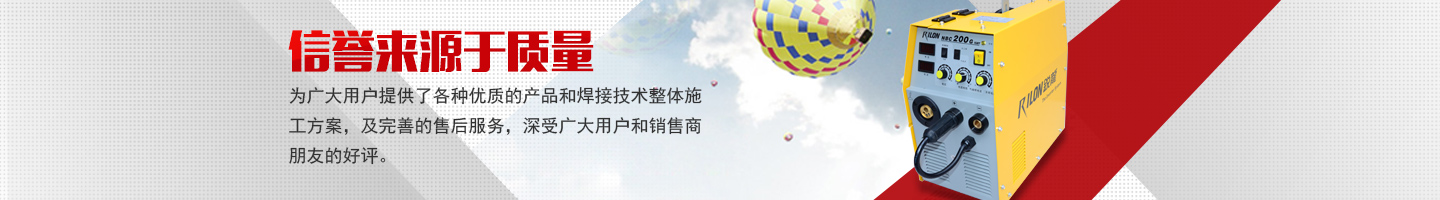
1990年代,中国引进苏-27重型战斗机并开启国产化仿制之路,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中国空军的装备体系,也引发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中俄技术合作与知识产权争议。俄罗斯从最初的“暴怒”到最终“理解”的态度转变,既反映了国际军贸竞争的复杂性,也揭示了双方在战略利益与技术博弈中的务实选择。

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急需外汇,而中国则面临空军装备现代化的迫切需求。1996年,两国签署协议,中国引进24架苏-27SK战斗机,并获授权生产200架国产化型号(即歼-11A),初期零部件需从俄进口,逐步提升国产化率。俄罗斯的算盘是:通过长期出售零部件和技术支持,将中国绑定为“长期客户”,从而维持苏霍伊设计局及共青城飞机制造厂的生存。
苏-27的引进对中国意义重大。它填补了中国双发重型战斗机的空白,其翼身融合设计、AL-31F涡扇发动机、多普勒雷达等核心技术,为后续国产战机的研发奠定了基础。

按俄方设想,中国完成200架歼-11A的生产后,仍需依赖俄制零部件。然而,中国仅生产104架歼-11A后,便转向自主研发歼-11B。该机型采用国产航电系统、复合材料、先进雷达(重量仅为苏-27雷达的1/4)和武器系统,性能显著提升。
这一转变令俄罗斯措手不及。2008年,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率团访华,抗议中国“未经协商”擅自改进苏-27,并指责中方侵犯知识产权。俄方的愤怒源于双重担忧:
歼-11B国产化率的提升,意味着俄方无法通过零部件出口持续获利;

中国可能仿效歼-7出口模式,以更低价格抢占俄制苏-27系列战机的国际市场。
面对俄方指责,中国提出两点关键反驳:
苏联时期对外军售以无偿援助为主,未强调知识产权保护。俄相关法律在中俄签署苏-27生产协议3年后才出台,且双方首份军事技术合作知识产权协议迟至2008年才签订,无法追溯约束歼-11B项目;
苏-27的雷达、航电等系统已落后于中国需求,改进是为了满足国防现代化需求,协议中亦未禁止技术升级。
俄方虽不满,但因缺乏法律依据,最终转向务实谈判。

俄罗斯的“暴怒”逐渐平息,源于中方采取的多项安抚措施:
歼-11B早期批次仍使用俄制AL-31F发动机,后续机型如歼-10、歼-20也部分依赖俄发,维持了俄方利益;
2010年代,中国追加采购100架苏-30和24架苏-35,既缓解南海局势压力,也为俄方提供新订单;
歼-11B、歼-16等衍生型号未进入国际市场,避免与俄制苏-35直接竞争。
此外,西方对俄制裁(如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)迫使俄罗斯调整对华战略,技术合作的重要性超过短期利益争议。

仿制苏-27的争议最终以“各取所需”收场: 通过逆向工程,不仅快速装备了歼-11B、歼-15(舰载型)、歼-16(多用途型)等机型,还催生了国产涡扇-10发动机和主动相控阵雷达技术,为歼-20隐身战机的诞生奠定基础;
苏-27项目带来的资金使其军工企业渡过解体后的生存危机,而中国后续的苏-30、苏-35订单进一步巩固了俄在国际军贸市场的地位。
从“暴怒”到“理解”,俄罗斯的态度变化本质上是现实主义外交的体现。中国在遵守合作框架的同时,通过技术自主化打破了外部依赖;俄罗斯则在权衡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后,选择了妥协与合作。这场风波不仅印证了“技术自主权即国家安全”的硬道理,也为国际军事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与战略利益平衡提供了经典案例。

技术转让的短期收益可能伴随长期风险,而自主创新才是打破技术壁垒的根本。中俄的博弈与和解表明,大国竞争的本质不是零和对抗,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共同生存的空间。